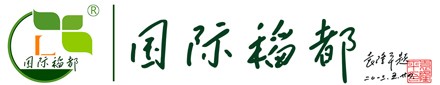


2011年8月,我接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夫人邓哲老师的电话,要我带老伴去长沙玩几天。
自从1990年3月袁隆平举家从安江农校搬迁到长沙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后,二十年间,我也记不清去过他家几次了,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有七,八次吧。
袁隆平为人随和,乐观豁达,淡泊名利且生性幽默。八十二岁的老人了,每天他忙完工作,就去散步,游泳,下象棋,拉小提琴或者与单位的中青年同事一起打气排球,隔三差五会找几个人来打几圈麻将,生活过的充实而富有情趣。同时,他还不忘随时随处找乐子,调侃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常常叫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他真是一个快乐老人,快乐老顽童!
乐不可支
袁隆平的家在长沙马坡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院内的东南一角,占地约1.5亩,属院中院。院中花木扶疏,风景宜人。他住的地方是中西合璧式的两层楼房,有十多间房子。他的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和事业。大多数时候,偌大的空间,就住着他们老两口,早些年还带着九岁的侄孙女邓林峰。
我第一次去袁隆平家是1990年4月到长沙出差。我是从怀化搭火车去的,坐的是硬座,经过了一个晚上的颠簸,次日早晨六点半钟才抵达长沙。
在袁隆平家吃过早饭后,我便在他们家一楼的客房里呼呼大睡。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钟了,中间邓哲来喊我吃中饭,我都谢绝了。
四月底的天气,气温陡升,一天比一天热,中午的最高气温已越过300C。那时他家刚搬来不久,还未装空调,我起床后,赤着脚,光着上身,慵懒地躺在靠椅上翻阅各种小报。
不知什么时候,袁隆平轻轻地走进房来,像个幽灵似的,没说一句话,只朝我瞄了一眼,又轻轻地走出去了。他走到厨房,与保姆刘姨说了几句话,只听见刘姨一阵轻笑,随后又与刚进门的春娣说了几句,春娣也笑出声来。春娣是邓哲的侄媳,小林峰的妈妈,常来姑姑家玩。
“袁先生又在搞什么名堂?”我不解地问自己。
接着就听见袁隆平在过道上喊话:“邓哲,快拿把剪刀下来。”拿剪刀,干什么?我正在狐疑不定之际,袁隆平就带着三位女士————邓哲,春娣和保姆刘姨一起走进房来。我猝不及防,连忙扯了一件衬衣披在身上。袁隆平指着我的脚说:“你们看看,周老师的脚趾甲有多长啊,都打转了。”邓哲一看,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啊哟,真是够长了,比慈禧太后的手指甲还要长。”
袁隆平只是傻笑着,三位女士则笑成了一团。此刻的尴尬不用说了,地上如有一条缝,我立马会钻进去。
邓哲将剪刀递给了我,我极不情愿地在三位女士面前将脚趾一一剪去…
晚饭后,袁隆平告诉我,今晚去长沙农校看望管校长。管校长名叫管彦健,年届八旬,是安江农校的老校长。管老从安江农校离休后,省农业厅为照顾他,特将他一家安排到长沙农校居住。
大约八点半钟,我们一行四人(含司机)驱车去长沙农校,邓哲带了许多礼品去,有人参、墨鱼、桂元,还有几箱水果。
真不凑巧,那天晚上长沙农校停电了。我们摸黑敲开了管校长的门,管老和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因是临时停的电,管老家连蜡烛都没有一根,于是大家便在黑暗中海阔天空的聊了起来…
不知不觉聊到了晚上十点钟了,我们便起身告辞。
小车开进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时,司机要放车进车库,我们便在车库旁下了车。
刚一下车,就听见袁隆平一声大叫:“完了,完了,去的时候,我将电水壶插上烧开水,现在不知道怎样了?”
邓哲一听,脸色大变,冲着老袁吼了起来:“你这个老东西,要你烧什么开水,人家刘姨下班前把所有的开水瓶都灌的满满的,要是失了火,怎么得了!”说罢,她便一头朝家里方向冲去…
被夫人骂了一顿的袁隆平,看着我在一边笑,怪不好意思,他拍着我的背膀,自我解嘲地说:“我的老爱人,对我太好了,我常年在外搞杂交水稻研究,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她担待,我欠她的太多了,她常使些小性子,我都让着她。”
这一刻,我的心里如同开了莲花,我看见了“杂交水稻之母”训斥“杂交水稻之父”那精彩绝伦的一幕!我不由得暗自笑道:“好你个老袁!今天白天故意出我的洋相,这下子,有你好看的啰。”
当我最后一个到达袁府时,袁隆平马上迎了过来说:“没事,没事”。“没事就好。”我连忙附和道。
原来,在楼上的小林峰,做完了作业后,下来解手,看见客厅里的水壶开了,顺手把电源拔了。
“好险啊,多亏了林峰。”袁隆平虚惊一场后说。不一会,他又来劲了,朝着楼上喊道:“林峰你是个好孩子,姑公喜欢你,你崭劲读书啊,将来姑公送你到美国去留学。”
这时,邓哲的气已消了一大半,但对老袁还是有点愤懑:“你发什么神经啊!林峰早已睡着了,人家明天早上六点钟就要起来上学,你硬是要把她吵醒才快活?”
袁隆平知趣地去了卫生间…
穿着得体
袁隆平在单身时代,不修边幅,太不讲究了,他的床脚、枕头下、抽屉里到处堆满了臭袜子、脏衣裤。自从与邓哲结婚后, 有贤内助的调摆,袁隆平一身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活象换了个人似的。只是还谈不上“时尚”,或者说,还是有点土气,加上他理的板寸平头和长年在太阳下被晒的黝黑的脸庞,不知闹出过多少笑话。
有一次,他应邀去贵州讲学,在火车软卧车箱里,因为穿着像农民,被列车员推倒在地,直到他从身上掏出证件来,人家才相信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汉子,竟是享誉中外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还有一次,他接到国家农业部的电话,要他火速赶去北京与美国农业专家会谈。他去怀化火车站买票时,售票员听他说要买软卧票,瞪了他一眼,一句“没票了”就把他给打发了。后来还是我辗转找到售票处的负责人,说出了袁隆平的名字,人家才给他解决了去北京的软卧票,没有误他的事。
如今,袁隆平在穿着上,依然保持着朴素、大方、得体的风格。他平常还是习惯性穿着那种轻便的休闲服,脚上穿的是十块一双的的圆口跑鞋。但每遇正式场合,如外出开会,讲学或在中心接待中外嘉宾和省部级领导,他必在家扎扎实实地“梳妆打扮”一番。袁隆平深切地意识到,他的着装是否得体,不只是他个人的事, 而是代表了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形象。
每次出发前,他身着笔挺的西装,系上鲜艳的领带,脚蹬锃亮的皮鞋,会主动地站在邓哲面前,接受夫人的“检阅”。邓哲踮起脚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再扯扯下摆,然后围着他转一圈。“行啊”一俟邓哲发出“合格”的指令,袁隆平才高视阔步地走出家门。
不仅如此,他还关注身边的同事和朋友的衣着穿戴。
有一次,袁隆平在客厅里对我说:“我说,周武彩呀,你也是个副教授了,也该备两套好衣服,别老是几十年一贯制,总是穿那几件老掉牙的旧衣服。”
我点头同意,表示这两天就去买服装。
没曾想,他竟走出客厅,对着楼上大声说:“邓哲,你把我的西装拿两套下来,拣好的拿啊,送给周老师。”
不一会,邓哲就捧着两套西装从楼上下来。
我说:“我不要你们的衣服,我刚才讲了就去买的呀!”
这两套西服,有八成新,全是毛料,质地绝对上乘,一套是藏青色,一套是浅黄色的。
他们不容分说地就推搡着我试穿起来。袁隆平身高1.70米,而我只有1.65米。这一穿不打紧,下摆已到了膝盖。
袁隆平夫妇笑过不停,邓哲说:“你拿去裁缝铺改一下”。最终我还是坚持不要,邓哲才又将西服收起来。
袁隆平又跑到楼上,拿出一件麻纺西装穿在身上,对我说:“小吴门有一家名叫培罗蒙的商店,我这件西装就是在那里买的,价廉物美,我还穿着去了美国哩。今天若不是有位副省长要来,我就陪你去。”接着他还叮嘱:“记住我穿的这件是76的,你买72的就可以了。”
当天下午,我就买回一件与袁隆平同一品牌的麻纺西装。
事后,有好些同事说:“你真傻!袁院士送给你的衣服,你穿不上,也可以留着纪念啊。”
可惜,当时我脑子里少了这根弦。
饮食清淡
袁隆平为了研究杂交水稻,几十年如一日在外劳碌奔波,居无定所,吃的更是不尽人意。长此以往,他的肠胃出了问题。他不仅吃的少,而且一贯追求清淡。
平常他家就是两荤两素或者一荤多素,有时,晚餐老两口就下一碗光头素面对付一下。
他的早餐也极为简单:一碗稀饭,一根油条,外加一片面包。餐桌上摆有鸡蛋、牛奶和肉包他都不吃。他说,家里人说的次数多了,他一个星期才吃一个鸡蛋。
当然也有例外,如家中来了客人,必多加几道菜。有一次,我带着一个年轻的同事去他家玩。他们弄了一大桌菜款待我们,有鸡、有鱼、有卤鸭子,还有海鲜肉丸等。我注意到袁隆平,只顾吃蔬菜,间或喝点肉汤,对荤菜是无动于衷,没见他动筷子。邓哲也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爽了一片卤鸭子,就再也不吃了。我这位年青的同事是第一次到袁隆平家,十分拘谨,吃饭时,老时把头低着,不敢看袁隆平,我示意他把头抬起来,说:“吃啊!到袁先生家,不必讲客气。”于是,我们加快了吃菜的节奏。那一大盘色香味俱全的卤鸭子和第一次吃到的海鲜肉丸,最后被我和同事风卷残云般扫荡净尽。
袁隆平有一个好习惯,他最喜欢吃水果。他家常备有香蕉、柑桔、苹果、梨子等多种水果。他从早到晚吃不不停,他宁肯少吃一些饭菜,但决不可一日无水果。这或许就是他唯一的特殊营养和保健的重要方式吧。
袁隆平只抽烟,不喝酒。现在年事已高,烟戒不掉,家人和同事就设法给他弄来日本、台湾的烟。
那种烟,焦油量几乎为零,我有一次连抽四支,都觉得跟没抽烟似的,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家人和同事的一番苦心。
袁隆平虽然滴酒不沾,但他家却有好多好酒。
有一次,在开餐前,他把我带到进门的拐角处。他顺手揿亮电灯,这里放置着一个两层的玻璃酒柜。
哇噻!里面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全是好酒啊!
有茅台、五粮液、酒鬼酒,还有法国红葡萄酒,满满一柜子,足有二十多瓶。
袁隆平告诉我,这些酒都是逢年过节,亲戚朋友和同事送的。
以前,他的大儿子应酬多能喝酒,现在大儿子居然把烟、酒都戒掉了,那么这些酒摆上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会一一回赠给亲友和同事。
袁隆平从酒柜中拿出一瓶茅台酒说:“今天,你喝点茅台吧。“我说:“我不喝白酒了,我现在只喝点葡萄酒。”
袁隆平指着下面一格说:“这里有高级葡萄酒,你自己选一瓶吧。”
我一看全是外文标志,便说:“我不喝外国的葡萄酒,我只喜欢喝中国的民权葡萄酒。”
袁隆平招呼我先去餐厅坐下,他说:“好像是有一瓶民权葡萄酒。”
表示这就去取来。
餐厅的餐桌上,摆满了一桌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菜肴,邓哲、小林峰还有保姆刘姨都齐齐地坐到了桌边。邓哲说:“袁先生又干什么去了,等下菜都凉了。”
不一会,袁隆平从楼上下来,转身又进了厨房,他终于找到了一瓶民权葡萄酒。
袁先生把这瓶酒递给我说:“你慢慢喝,随意啊!”我接过酒瓶,手上立即有一种滑腻的感觉,掀开盖子,闻了一下,一股油腥味冲鼻而来。我立马站起来说:“这不是酒,这是油啊!”
邓哲赶紧走过来问袁隆平:“你这是从那里拿来的。”老袁说:“就在厨房的灶台上。”邓哲笑了起来:“这是我放在厨房的一瓶清油啊!”
我对老袁说:“好啊,你叫我喝油,你想泻死我呀!”话音刚落,邓哲和保姆刘姨一阵捧腹大笑,小林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还直喊肚子痛,她把整个身子都扑到了姑婆的怀里…
事业第一
1964年2月,34岁的袁隆平与自己的学生,年届26岁的邓哲喜结连理,他们都是大龄晚婚的人了。
他们过去都曾有过各自美好的初恋。袁隆平的初恋对象是马路对过、省重点中学—黔阳一中一位被称为“校花”的化学老师,邓哲的对象则是一位年轻英俊的解放军军官。
在“文化大革命”那极“左”路线盛行的年代,他们都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在婚恋场中双双败下阵来。
后经学校一位同事的牵线,袁隆平才相中了邓哲。两颗受伤的心, 一经碰撞便擦出了激烈的爱情火花。
婚后,袁隆平夫妇,情真意笃,举案齐眉,他们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是安江农校人人羡慕的幸福之家。
俗话说:“牙齿也有碰着舌头的时候”。1989年2月的一天,我在不经意间,遇上了他们夫妇的一次激烈的争吵。记得那天下午,我路过袁的住处,听到里面传出一阵女人呜呜的哭声。我立即掉头走进了袁隆平的家,在餐厅里看到一脸凝重的袁隆平站在那里,旁边的邓哲还在嚎啕大哭。
我沉着脸问袁隆平:“袁先生,怎么回事?”邓哲见有人来了,便大声嚷道:“你要周老师来评评理,他是个木头人,只要事业,不要家庭。”
还未等邓哲说完,袁隆平一把将我拽到客厅里说:“邓哲吵着要调到长沙去,不是不可以,只要我一句话,马上就能办到。”
我打断老袁的话说:“你为什么不肯说这句话呢?”
原来袁隆平对这件事有他自己的打算和苦衷。
1976年3月,邓哲从距安江农校20多公里的黔阳县(今洪江市)农科所调进学校。照理说,他们夫妻分居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其实不然。因为这个时候,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已获成功。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决定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这时,袁隆平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总是马不停地到全国各地去作技术指导,在家的时间更少了,忙得分身乏术了。他们夫妻仍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1983年省里将袁隆平调到长沙,要他负责筹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邓哲提出要跟他一起去,以便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袁隆平没有答应。
1984年6月15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袁隆平任中心主任。邓哲又一次提出要调到长沙。老袁还是没有答应。这期间,袁隆平从安江农校一下子就调去了他的十名助手到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唯独没有调邓哲。
要调邓哲去,不仅在情理上说得过去,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确实只要袁隆平说一句话,马上就能实现。
老袁为什么硬是不肯说这句话呢?难道他真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懂得至爱亲情的木头人?不是的!袁隆平其实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性情中人,他何尝不想与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呢?
他是将杂交水稻事业与个人的家事放在天平上,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袁隆平说:“新建一个单位,谈何容易,要全面规划,大搞基建,招聘人才,广泛搜集各类资料…万事开头难啊!”
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工作,他打算先招聘相当数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以便有序地开展工作,迅速打开局面,他不想先调家属去,怕影响整个工作的进程。
于是这才不可避免地在他们夫妻间发生了这次冲突。
直到1990年3月,邓哲才如愿以偿地调到长沙袁隆平的身边。这一年,袁隆平已经60岁,邓哲也是52岁了,他们夫妻将那大好的青春年华,全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杂交水稻事业。
我这次去长沙,是去年10月底成行的。老伴身体不适,没有去。
袁隆平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袁先生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的气色不错啊!退休了,还在忙什么呢?”
我据实以告:“听课、写字和钓鱼。”邓哲老师马上拿起电话,把在中心工作的原安江农校的老同事都叫来与我见面、聊天。不一会,老同事们都赶了过来,他家的客厅顿时就热闹起来。
袁先生只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他把安江农校至今尚健在的老同事的近况都逐一问到了。
他太忙了,前天才从杭州、福州和南宁三个省会城市讲学回来,此刻又要忙着去办公室看文件和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下午,几乎每天都有一拨又一拨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友人等着与他会见。
2011年袁隆平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实现了超级杂交稻大面积亩产突破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在前不久评选出的“2011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中位列第三。如今,他又马不停蹄投入到在他90岁时,实现超级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的战斗中,要为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实在不忍再打扰他们,谢绝了他们的挽留,只呆了两天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