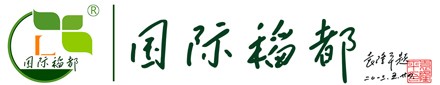

新华网长沙2001年11月5日电(记者杨善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在农村采访中就与袁隆平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八百里洞庭到湘西山区,从长沙东郊的试验田间到海南岛育种基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袁隆平先生从安江农校一个普通教师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功勋科学家”,在杂交水稻研究工作中走过了30多年的风雨征程。他先后获得国务院特等发明奖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及多项国际大奖,几乎每年都有新品种或研究新成果出现,在他和他的周围经常有新闻发生。我对袁先生身边发生的重大新闻都及时采写,前后发稿数百篇。多年来,我因为报道袁隆平,曾多次获得新华社和省里以及其他方面的奖励。
袁先生所在的湖南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现称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地处长沙市郊,原属长沙县境内,现今划归芙蓉区管辖,离城市中心较远,交通不方便。多少年来,我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晴天雨天,只要有采访任务在所不辞,即使无采访任务也要常去看看,听听情况,增加一些感性认识,积累一些资料。
袁先生现在的工作规律大体上是“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湖南农科院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进行学术活动,三分之一在海南育种和各地参加会议。根据他这种工作生活规律,我在采访中尽量多到第一线去,熟悉试验育种情况。海南岛育种基地有独特的自然条件,是加快杂交稻繁殖育种进度必不可少的地方,袁先生和许多育种家及农技人员每年似侯鸟一样冬去春回,在那里撒下了辛勤的汗水,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科学数据,育出了一批又一批新种子。特别是在海南岛育种基地,看到许多育种家和科学工作者像农民一样,不怕太阳晒,不怕生活苦,工作得很起劲,我从中受到心灵的震撼和教育。通过跟踪采访,我对袁先生和他手下几个骨干科研人员更了解更熟悉了,成了“他乡遇到的知已”,他们有什么新闻就告诉我。
1995年8月下旬,袁隆平先生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了,他通知我去怀化山区参加一个会议,并告诉我会有好消息。出发那天下着雨,我们一起到了目的地,看到农业部和国家科委的同志到了,还有外国朋友,但是只有少数几个记者。第二天会议开始就进行连续参观,我们在山间小道上,冒雨行进,看了许多丰收的两系杂交稻田,还有一片片高产制种田。代表们一般都是白天看,晚上议。几天后,袁隆平在怀化宣布我国两系法杂交水稻基本培育成功。我和另一个记者合作在现场采写了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第二天新华社播发后,全国许多报纸都纷纷刊登,湖南日报和长沙晚报均登头版头条;广播电视新闻也随时播出。这是继1973年三系杂交水稻基本选育配套成功以后又一喜讯。它将对中国今后粮食增产起着重要作用。这篇稿件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较大反响,被湖南省评为当年优秀新闻,次年5月,又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中国新闻奖。
袁先生的研究是从怀化安江农校起步的,这也是我多次采访过的地方;岳阳、长沙、醴陵、湘乡等地市是袁先生进行两系杂交稻示范的基地,我常去采访,有的地方一年要去几次。早稻黄熟之时,正是“三伏”炎热天,江南的烈日似火,这时下田观察杂交稻,免不了要湿透衣服,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我常在采访包里多带上一件备用汗衫和一顶能收拢打开的布草帽,久而久之,一些熟悉我的农科人员笑称我是“农民记者”。就这样,近30年来我从袁隆平所研究的三系杂交稻到二系杂交稻,再到超级杂交稻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许多报道素材,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写出第一篇新华社对外新闻《中国杂交水稻实现全面配套》,报道袁隆平的科研事迹起,到今年,我先后写了《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合作稿)、《他有凌去志》、《绿色革命大元帅》、《东方魔稻创始人》、《袁隆平和他的超级杂水稻》、《不要忽视杂交水稻》、《琼岛为我国杂交稻育种作出大贡献》和《杂交水稻造福全人类》、《湖南重奖袁隆平》等,比较及时地记录了袁隆平和他从事研究的重大进展。由于我长期把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作为采访基点,常接触袁先生和他周围的同志,交了一批新老朋友,所以工作起来比较顺手。
袁先生是著名的农业育种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学识渊博。而我要报道好袁先生本人的先进事迹和他研究杂交稻的重大成就,必须坚持多学多问,才能弥补我的农学知识不足。我觉得除了向书本学习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包括识别稻种,看禾苗长势,了解各种杂交稻的特点等等。参加现场会议也是一种学习,读论文,听专家发言,处处都有学习的机会。学习是为了“进补”知识,同时也是防止报道出差错。这方面我深有体会。湖南省一个单位曾经搞了一种“玉米稻”的材料,即把玉米的基因转移到水稻植株上,在试验田里表现良好,生长茂盛,有较强的优势,然而一到大田中却表现逊色,甚至造成减产,只长茎叶,稻子很少。在没有通过品种审定情况下,有人就在广东和其他一些地方到处推广,当时袁隆平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农业部门,认为推广“玉米稻”要慎重,他也向我谈过此事,我及时将袁先生的观点整理出来,写成专家建议发表在《经济参考报》和其他报刊上,避免了一些损失,减少了赔产事件发生。当时,有的人听不进去,仍主张卖种子,强行推广,想得到一些暂时的经济利益,谁知到秋天。凡硬推的地方纷纷要求赔产的事件发生了,这个卖种单位的门窗都被减产的农民打破了,屋里的电视机也被搬走了,最后还是通过多方协商,赔了一部分钱才算了结。
对名人的报道要十分慎重。关于超级杂交稻的报道我一切从实际出发,从重大突破到基本实验成功,一就一,二就二。我自始自终认为科技报道要讲科学,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写作,宁肯少发一篇稿子,也不在复杂情况之下讲过头话。
综上所述,此前我在报道袁隆平和杂交水稻方面虽然发稿较多,但迄今为止还未出现过差错。因为我始终坚持向内行求教,凡重大新闻一定送袁先生或其他专家审稿,在一些新闻竞争的关键时刻尽量做到迅速准确,坚持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我在长期采访袁隆平先生的过程中,始终注意保密,不抢发新闻。比如,今年2月19日,袁先生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事,我在1个月前就从袁先生那里知道一些风声。他为了让我们心中有底,事前透了风,但他交代,何时报道,如何报道,一定要按规定办,我遵守这种“君子协定”,只把这一情况向社领导个别汇报,坚持按上级统一规定进行,等到可以报道的时候我们配合总社及时发了新闻,还有相关背景资料,丰富了新华社报道的内容。多年来,我写的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的报道多次被总社国内部、对外部、《了望》、《经济参考报》等评为好稿,多次获得过省里的优秀新闻奖,在社会上,读者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报道袁隆平的先进事迹,促进杂交水稻事业的发展起了应起的作用。有的内部报道反映了杂交稻发展的情况和困难,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他们作了重要批示,推动了实际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使我难忘的是1994年6月15日,庆祝杂交水稻研究成功30周年的时候,我和分社另一名摄影记者被授予首届袁隆平杂交水稻基金奖,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新自发给我们奖牌、奖金,使我深受鼓舞。
今年1月16日,袁先生在他的办公室约见我和另外两名记者,并亲自颁发给我们每人一本红色的荣誉证书,给我的证书上面写着“我们新闻界的好朋友——杨善清同志”,同时袁先生还与我们分别合影留念。他客气地表示感谢我们长期对杂交水稻科研事业的支持。回顾过去,我想,我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要不是袁先生和其他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哪有我们的新闻报道呢?要不是新华社把我培养成为“农大哥”,也不会有这种采访写作的机会。